TOPMEDIA
顶思传播
9岁女童被3000亿身价董事长性侵!拿什么保护我们的孩子?
来源:
|
作者:Alvin
|
发布时间: 2019-07-05
|
1024 次浏览
|
分享到:
恶魔再度降临,人性的黑暗,孩子们的安全守护,该从哪里入手?
刘文利教授认为,孩子对“熟人”侵害者的服从,与许多孩子在观念上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威权”影响有一定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培养孩子说“不”的勇气和平等的观念,让他们明白儿童性权利的重要性。
02 青春期恋爱
“性与健康行为”核心话题中,学生们在四年级学习性萌动和性幻想,在五年级了解了青春期爱情。性教育不仅传递性知识,也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技能。
刘文利教授认为,性教育的课程目标之一是教会孩子,如何了解自己的情感,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表达了,别人接受了,应该怎么去做?如果别人拒绝了,又要怎么做?在教会孩子珍视自己情感的同时,又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情感。”
03 单亲家庭教育
在实际调查中,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避讳谈及自己的家庭关系,刘教授选择在性教育人际关系的教育中引入多元家庭的内容。她认为,这有利于让孩子懂得,要尊重来自不同家庭的伙伴。在多元家庭的内容中,孩子会被教导:无论生活在家庭中,孩子都应该得到关爱和幸福,父母离异并不代表就不爱孩子了。
性教育教师该如何炼成
“我必须要在教学一线,我才有发言权,否则就不知道性教育课是什么样的。”多年来,刘文利教授和她的团队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的一些学校合作,培养了一批性教育教师,这些教师不仅能够独立给学生教授性知识,也成为了培训其他老师成为新性教育老师的人才。
此外,只要有时间,刘教授也一定会在性教育的课堂里,获得性教育的一手反馈资料。现在,在北京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把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开设,性教育课被排进学校的课表里,有经过培训的老师给学生上性教育课。
 刘文利教授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图片源自搜狐网
刘文利教授于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图片源自搜狐网 回望自己与这些学校开展性教育合作的经历,刘教授认为一名性教育老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教学知识以外,还有三步路要走:
第一步:对性和性教育多一些积极美好的态度
对于刘教授而言,在培训老师时最艰难的就是如何让老师们抛掉“羞耻心”向学生传授性知识。
一位实验学校的老师第一次为班级开展性教育,课前她生怕一旦谈起性,学生们就会“炸锅”,但结果出乎她的意料,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得非常“平静”,这对教师的自信心是很大的鼓舞。
在许多实验学校的实践结果表明,如果老师能够首先放平自己,摆脱“害羞”,坚持以平静的态度向学生传授知识,学生是很容易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中去的,这是因为学生对性本身就有学习的欲望和兴趣,性教育课就是一门“自带流量”的学科。
刘教授对此还表示:“这一点和初中才开展性教育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一些对性的偏见和误解已经比较根深蒂固了”。
刘教授及其团队曾对实验学校中接受过性教育的学生进行追踪,在一堂生物课中,当老师讲解到性器官时,没有受过性教育的学生马上“炸锅”,或哄笑或鄙夷,而实验学校的学生则“泰然处之”。可见,提早实行性教育能够较好地帮助学生客观、真实、坦诚地了解性,理解性,大大降低了教师授课的难度。
第二步:多一些课堂讨论
在正常授课之外,刘教授也鼓励老师通过寻找和发现日常话题,引入课堂讨论,保证学生真正掌握了性知识。而令刘教授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五年级学生的关于关爱艾滋病病人的课堂讨论。
在课堂上,老师向学生们展示了一段视频新闻。新闻的内容是某市的一家机构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学生提供专门独立的考试地点。在观看完后,老师向学生提问对这一新闻的看法。
不少小组经过讨论都十分明确地表示这是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因为他们都知道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在一个教室里学习或考试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老师抓住这一话题继续向学生抛出了问题:“如果在你身边有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同学,你愿意和他在一个教室里学习吗?”孩子们表示愿意,认为与他们共处一室并没有被传染的风险,而上学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刘教授还提示,在进行课堂讨论时应该注意遵守“不加评判、有所引导、扭转偏见”的原则。
“性教育课不是数学课,1+1等于2是标准答案,应该尊重学生的发言和观点,不做过多的评判,但是如果讨论本身存在不尊重他人,或歧视,或偏见,那就需要老师及时引导”。
第三步:多一些感情交流
“性教育是一种情感学习”,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也不能完全局限于课堂内。在课下,老师也需要成为学生感情交流的伙伴,性教育的课下引导既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待人接物习惯,也是老师了解学生心理动态,拉近与学生关系的有效途径。
在刘教授接触的合作对象中,就有一位三年级学生,这位学生来自离异家庭,常年与妈妈分离,在她心中,妈妈的离开是因为妈妈不爱自己了,因此也很少与妈妈联系。这位学生的心理状态被性教育老师和班主任了解到,给予及时开导,这位学生在性教育课上学习了“结婚与离婚”的内容,懂得爸爸妈妈虽然离婚了,但依然会爱着他们的孩子。在母亲节这一天,这位学生主动打电话给妈妈,在电话里第一次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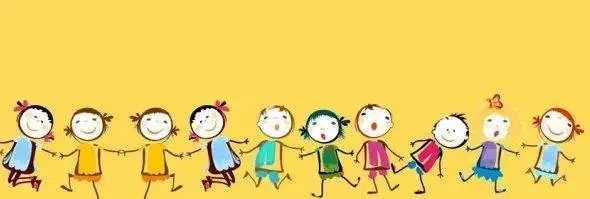
“性教育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很多事情越早准备效果越好,才能事半功倍。”多年的努力让刘文利教授带领的团队取得了性教育的诸多成果。
目前,刘教授和团队在研发初中性教育读本。课题组从今年2月份起与北京一土学校开展更深入的性教育合作,她也赞同国际学校将会是中国性教育落地生根的一个理想场所。但她坦言目前在国内推行性教育工作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2017年,《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在网上引起全国范围的讨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刘文利教授表示,性教育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教育领域,有争议是好事,在争议中大家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性教育对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路漫漫其修远兮,学校教育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防范悲剧事件的发生,需要全民教育。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缺一不可。比起孩子的性教育,或许成年人的性教育,更为重要!
不然,谁又能保证,下一个被恶魔盯上的孩子,不是自家或者你身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