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说话达人秀节目《奇葩说》意外走红的哲学教授刘擎走出荧幕,与一群00后探讨“如何用哲学思维来应对焦虑?”00后们到底有哪些纠结?纷繁复杂的焦虑背后是否有章可循?看这位“奇葩”导师如何破解。
文 | Zoey
编 | Chris_guo
第七季《奇葩说》请来哲学教授刘擎担当辩论导师,他和经济学者薛兆丰的“对战”几度燃爆全场。其中,两者关于“理想与现实之争”成为了节目最大的亮点之一。和“务实派”代表薛兆丰不同,刘擎显然是“理想派“,他不断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去反思。
在接受人民文娱采访时,他说了一句极具感染力的话,“你心中尚存的不满,就是第一行诗。”这可谓对当下深处困顿之人的莫大鼓励。
近日,刘擎在华夏基金·2021哈佛AUSCR青年峰会上对话00后,探讨“如何从哲学的视角诠释内卷背景下的焦虑问题”,其回答令人醍醐灌顶。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季《奇葩说》导师。著有《西方现代思想》、《纷争的年代》、《权威的理由》等作品。
为便于阅读,以下内容以第一人称呈现
01
焦虑从何而来?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要深挖一个大的背景——现代性的困境。
现代性的焦虑来自现代社会的两种压力——工具主义和唯我论,而这两种压力恰好是冲突的。
先来说说工具主义。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我们不是热爱它本身,而是把它看作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我们自己又是不清楚的,好像是别人给的。比如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可以说,相当一部分人追求的是财富、权力、名望,这几乎成为全球共识,尤其是财富。
再来说唯我论。它是指一件事情好不好,它没有客观价值,而是你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
这两者的冲突性在哪里呢?工具主义是社会文化取向,这些目标是流行的,我们本身没有反思它们,而生活意义完全要靠你自己创造。在工具主义和唯我论的双重压力下,就形成了现代人的焦虑。
举个例子,大家都想去名校读书,比如清华、北大、常春藤学校,这些学校的校训都是深刻和博大的,没有一所学校教你追求功名和富有,但是很多学生毕业出来以后就是在追求狭隘的功利性目标,这就是冲突。
02
内卷≠竞争,而是意义感的丧失
遇到这样的问题,哲学的应对方法是什么呢?古典意义上,哲学被称为追求智慧。这里面强调一种反思的意识或者反思的能力。什么是反思?它是指我们在过一种生活,同时有能力抽身出来,把自己的言行和处境看作对象,来反观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主体,可以把自己的言行客体化,观察到我们之所以如此行为的深刻原因和驱动它的利益,这是一种哲学方法。再换句话说,你和现在的处境拉开一个距离,你站在一个第三人称的位置上看待自己。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意识,但是你要把它发展成自觉和有力量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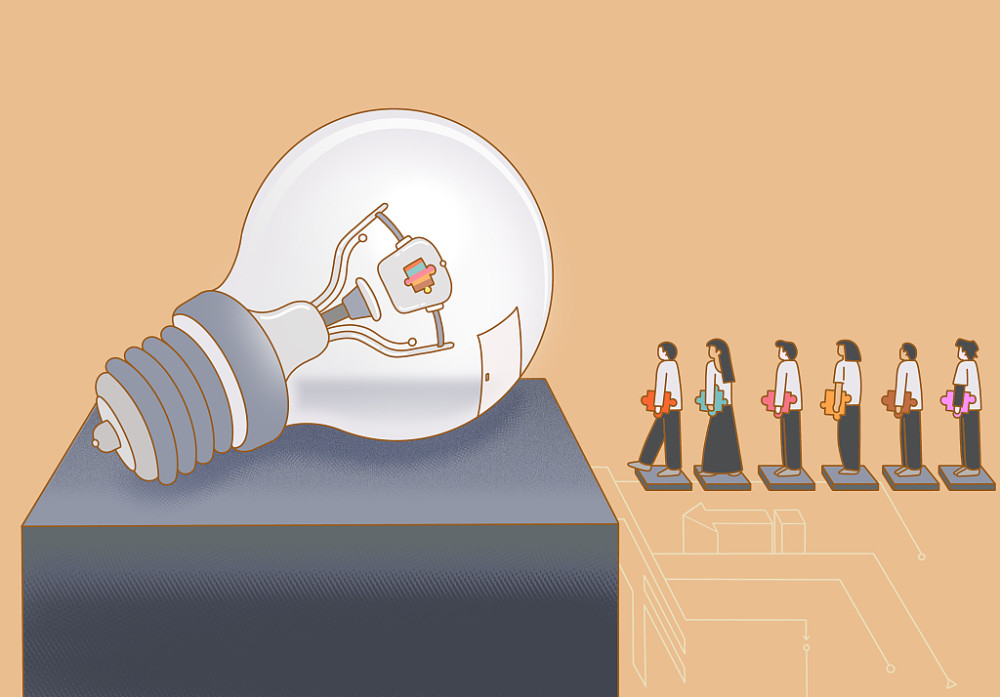
回到“焦虑”的问题。是什么造成现代性的困境?在现代社会,宗教压力和传统道德开始越来越边缘化,它不再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支柱,社会的发展依靠分工,分工把人变成工具。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转变,成为取用关系(utility instrumental)。这就好比,原本大自然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安居在里面。但是现在,我们把大自然客观对象化,大自然就变成了自然资源。
人也是同样,人生活在三重关系里——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那么,我们跟他人的关系也变成一个取用关系。我们所谓的朋友,很大层面上是有用的朋友。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变成享乐的工具,比如吃东西、打游戏,我们都是在把自己当成一种感官工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我们发现人才培养就是培养有特定功能的人。只有这样,社会整体在物质层面才能有比较大的进步和繁荣。当然,这个效果确实非常显著。我们学校的发展是从19世纪开始,普鲁士认为公立义务教育就是要把孩子按照军队的方式组织起来,同一年纪,同样的教材,最后培养出对社会有用的人。
功能性的单一取向导致人的培养目标是功能化的。我们在意的是,你能做什么,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教育里有一个现象就是,虚假的化约论等式。比如:父母都希望孩子幸福,这是非常天然的情感。等孩子长大一些,我们就把孩子的幸福简约(reduced)成“有出息”,有出息就要出人头地,出人头地就等于财富地位。最后,教育就演变成上名校,那么,初中、小学、幼儿园都要进好学校。最终,竞争就变成了一场战争,就像之前的口号:提高一分,干掉千人。
但是,人是非常丰富和全面的。学校教育应当是一个过程,一个共同体,这里面有情感价值,有归属感,有丰厚的关系,现在我们都简约化了。所以,这就是工具主义的代价。也就是,我们不关心你的个人价值和道德。只要这个道德和功能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不在乎。
现在,大家都在谈内卷,内卷和竞争不是同等的。竞争不等于白热化的内卷,内卷是一种高度竞争,在一个低级的、单一的模式里重复的竞争,才叫内卷。这样一种竞争带来的是意义感的丧失。
03
成功,是蓬勃茂盛的生长
为什么古代人没有这么多困境呢?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提到,古代人不需要有自己的剧本,他们的生活是有章可循的,变化非常少。但是现代人,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剧本,每个人都要独自原创自己的生活,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

1974年,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罗伯特·诺齐克做过一个叫“快乐体验机”的思想实验。实验内容是,假设把你放在一个机器里面,将你的感官封闭起来,然后给你的大脑接上很多电极,给你各种各样的刺激,让你能够梦想成真。比如:让你享受各种美味大餐、美妙的音乐等。他问,如果有这样一个体验机,你愿意一直生活在其中吗?
这是一个哲学思想实验,它设置了一个变量——自我感受良好(make you feel good)。实验者问,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变量,是不是就够了?在罗伯特教授看来,这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生命是一个进程(process), 这里面有故事,它不是将每时每刻美妙的感受简单加在一起就能构成一个幸福的人生。比如:我们都想考试得100分,有一天老师来到课堂上说,现在送给你们每个同学100分,瞬间大家会很高兴。但是,之后会很失落,因为你没有为了拿到这100分拼搏的过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目标和过程是不能够简单分开的。
如果把我们的人生比作一个电影,即使是喜剧电影,也不会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而是充满着冲突和挑战。所以,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长非常重要。
谈到快乐和幸福,英文叫“well being”,很多人翻译成“福祉和安康”,这是不准确的。“Being”是存在,“well being”是好的存在。而好的存在,不光有过去和现在,还应当有对未来的想象。这些阶段包含挫折和挑战,当你克服它的时候,感受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快乐,而是深刻的“wellbeing”。
简单来说,幸福和意义感相关。也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们享受做这件事的过程。比如:有的同学就是喜欢刷题,你也不用管别人告诉你,刷题没有用。有的人认为,能够解决问题,迎接挑战就很幸福。还有的人认为,快乐来源于别人的肯定和自我肯定。“承认”是黑格尔在“自我意识”理论里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现在有一个麻烦是,我们这个“承认”的“标的物”太单一了。比如:在中学、大学,标的物基本上就是分数,到了毕业以后就是财富。
为什么一个人的善意、美德、勇敢、正义感不能成为竞争的标的物?在现代社会,一个人是否有正义感,往往只有周围的人知道,但是钱是全世界通用的。
现在,教育经常把培养个性化的人和培养一个成功的人放在一起讨论。其实这两者不矛盾。关键是,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哈佛大学教授提过一个词叫“human flourishing”,他认为成功就是繁盛蓬勃地生长。他在2014年提出,全世界的五种普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