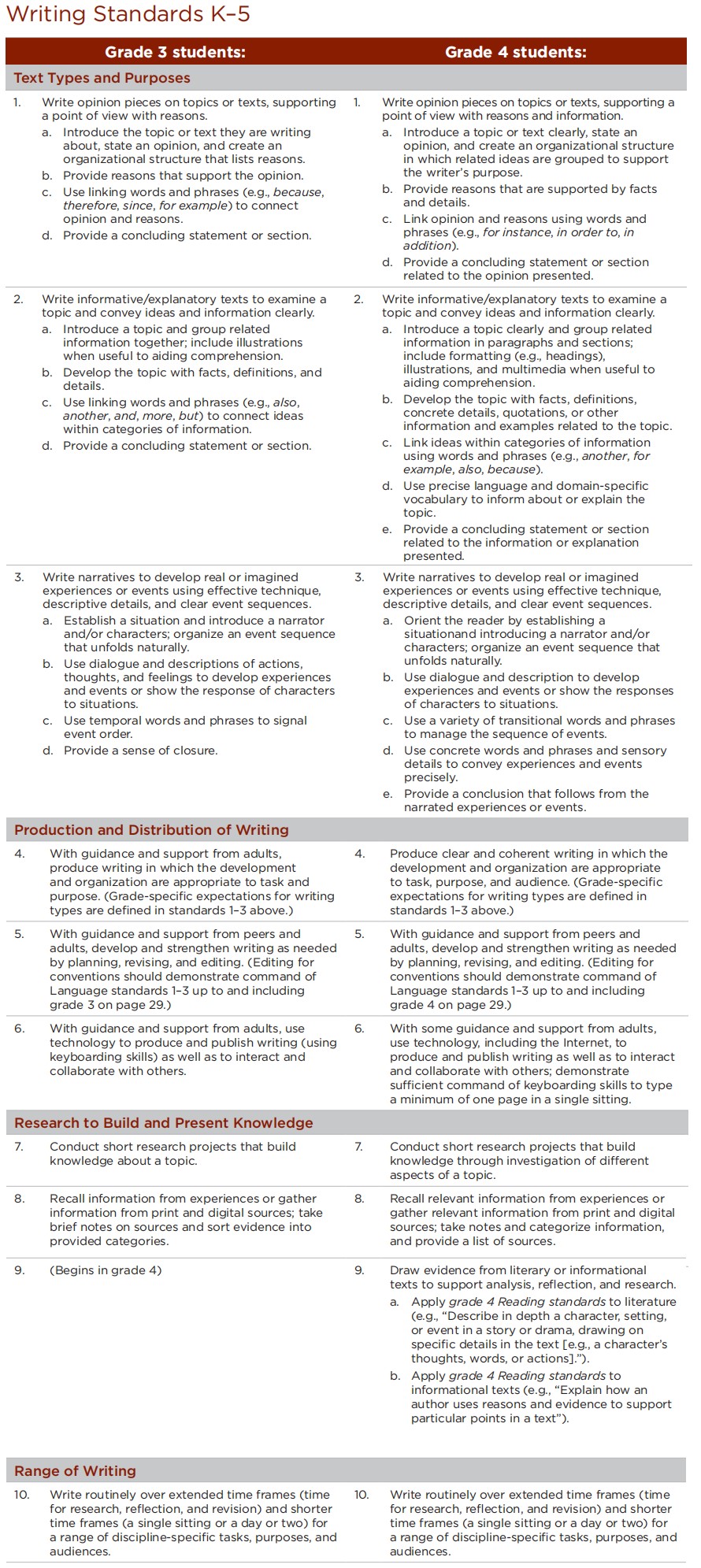
顶:您的媒体从业经历对写作课程的开发和写作教学,有什么帮助?
田:刚到学校时,我还是有意识地努力“清空”自己,扫除主观执见,更快接纳对我来说尚属新事物的“教育”。但做着做着,才醒悟以前的媒体经历,才是支撑现在工作的最大宝藏,是“原力”所在。怎么说呢?
首先,二十年的媒体写作,就是二十年天天在搞”真实写作”,这让我再也无法代入那种虚假的写作环境中。这个免疫力还是珍贵的。
第二,好像特别能理解美式写作教学,因为原来从事的媒体写作,没有中西之别。好玩的是,一些写作教材和藤校写作教师,提到一些具体写作教学建议,我一看,这和以前指导记者写作一些“小把戏”是一回事啊。
还有,比如示范写作。以前教新记者,说着说着,就直接在电脑上写给他们看。现在课堂上,我也尝试和学生同时写,不是和学生比高低,也不全是为了提供一个范本,而是要让学生看到,老师写东西,也会抓耳挠腮,要给他们展现一个涂涂改改的过程。
还有呢,在媒体做一个采访报道,和学生现在做的一些探究式项目,过程上很相似。对记者而言,写篇报道,先要从确定选题开始,然后搜集资料,提出问题,采访,再整理所有资料,确定思路,内容取舍,写作、修改、定稿,发表。以前,几乎天天和记者编辑做这样的“项目式探究”。把这些经验转换到探究式学习小项目中,比较得心应手。
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本能地将新闻热点事件引进课堂,有助于创设真实度高的写作情境。
顶:除了论证写作,未来还有什么新课程的开发计划?
田:论证写作课,针对八年级学生,这个年龄段是思维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接下来,我想针对六年级开发“信息写作课”(如何说清”事”和“物”),要援引媒体消息稿写作的训练方法。针对七年级,想开发“叙述写作课”(怎样能讲好一个故事),要借鉴媒体特写稿(非虚构性写作)写作范式。这两门课,要围绕“采访”来创设真实写作情境。
对我个人而言,当下最想搞一门诗歌写作课。左右脑需要平衡,论证写作太“理性”了。未来最感兴趣的,是想综合商业、科技、艺术、文学、媒体等多学科,搞一个有趣的项目。还没想好,应该挑战最大。
顶:从媒体到学校,角色转换很大,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心理感受?
田:好吧,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沮丧和欣喜交替往复的过程。
沮丧很正常,尤其对新老师。教学是一个人和人动态交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有不确定性,有意外,有落空。好在,那时候我正好读到一本书,作者是美国研究批判性思维的知名教授,在哈佛大学教过书。他在书中透露,上完每一堂课,他都会很沮丧,有时严重到要找心理医生。我看到这个,心里哈哈一笑,就不怎么怕自己的沮丧了。我明白了,哪怕有一堂课上得再得意,沮丧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堂课等着你。
欣喜来自你给学生带去的收获,来自学生的认可。今年春节后开学第一周,还没上课,有天中午在校园闲逛。远处一群上学期教过的男孩子,看到我,一伙人就飞奔过来。当中一个花坛,他们也不愿意多转个弯,直接翻过花坛,跳到我面前,问我这学期还教他们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这些男孩子在我身边欢呼跳跃。这是做老师的欣喜!
顶:最后,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平和学校?
田:有个好校长。万玮校长的教育主张,大家都很熟悉了。不过,他说过一句话,知道的人不多,我记住了,大意是要用办大学的方式办中学。这,令人向往。
有好学生。视野开阔,独立思考,思维敏锐,有才有艺。
有好老师。学校里真的有一批有想法、有情怀、有责任感、想创新的老师,很难得!
对了,还有一个好酷的教室。

图:部分田健东博士提供
采访小记:
对田健东博士的采访,跨时三个多月。先到平和旁听了他三次写作课,再约时间特别专访,采访后又马上邀请到他作为顶思TIDE2019的分论坛分享嘉宾。对作为码字工作者的我来说,受益匪浅。
在刚刚结束的TIDE大会上,田博士的“论证写作”分论坛和工作坊,也是被来自各地的国际化学校老师包围交流问题。促使着我们,把田博士一年多来在平和磨出来的一整套写作教学体系,好好整理出来。今天,干货满满的“鸿篇巨制”算是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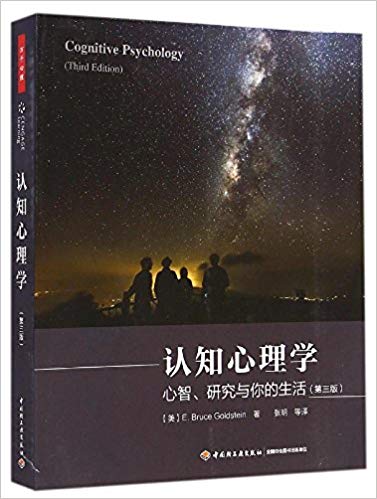
我们还请田博士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本来以为他会推荐写作书籍,没想到他推荐了一本《认知心理学》。因为他说,这本书让他领悟到,写作就是最基础的“编程”!归根到底,写作的套路,需要满足一个人基本的心理学认知规律。

